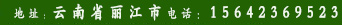|
编者按 王大闳,台湾现代主义建筑先驱,出生于中国上层社会之书香世家,后留学欧美接受建筑学教育,曾受教于现代主义大师WalterGropius和MiesVanderRohe,并与贝聿铭和PhilipJohnson是同学。建筑作品: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国父纪念馆、台北故宫博物院方案、建国南路自宅、虹庐、林语堂宅、台湾大学第一学生活动中心等。此外,曾译写王尔德小说《杜连魁》,著有科幻小说《幻城》。 年10月,由史建(“有方”创始人/策展人/建筑评论家)策划的“久违的现代”冯纪忠、王大闳建筑文献展在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上海馆展出,通过展示两者关于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的转化实验,探讨接续中国现代建筑设计。并由此关联的系列评论在线上线下展开,譬如王澍先说“在我们之前,真正革命性的建筑师,就是这两位,在大陆就是冯纪忠,在台湾就是王大闳”进而感叹先辈之努力和探索未得传承。(王大闳和冯纪忠都非常孤独刊于“有方”) 《乡愁经济》特约撰稿人华昌宜先生曾是王大闳先生的大洪事务所在台湾的首位全职雇员,现为王大闳建筑研究与保存学会理事长。华先生曾在《论述与回忆:王大闳》(徐明松著)中写过在大洪事务所的所见所闻一文,回顾他五十年前于王大闳共事的经验及观察。《乡愁经济》邀请华先生重新整理此文,以供关心王大闳建筑师的读者们有更贴近于他的了解。 在王大闳身边的所见所闻 年三月我从第五期预备军官服役退伍后不久,即毛遂自荐去了王大闳先生的大洪事务所。此后直至年秋去东海大学担任助教为止共在他事务所工作了两年半。最初事务所设在中华路,是与张昌华建筑师共用的一间日式平房住宅内。而大洪事务所内全职上班者仅我一人。绘图桌放在走廊光线较亮处。王先生则是在另一房间内,是否在内设计以及每天来多久已记不清楚。总之,好像我是他在上海「五联建筑师」结束,年来台再开业多年后雇用的全职人员第一人。在这以前,猜想他在接到委托案后是在家里做设计,然后工程施工图及监工必是借用其它建筑师(可能包括了张昌华先生)事务所人员来完成。因为记得在这以前曾在王先生建国南路自宅内看到他在一个绘图板上替清华大学教职员宿舍做的设计。相信在那个时代,就凭建筑师的这样一张设计图就可交给营造厂,再凭口头对材料及颜色的挑选就可建好住宅之类建筑。如果有施工图,那是营造厂的事(注一)。我怀疑,在年王先生在建国南路建造他那後来名满台湾的小住宅时,并未曾有过正式施工图,而是临场指示完成的。 不过我的工作却是对较大建筑绘制工程施工图,另加必要的设计。第一批是中兴新村的建设厅等几座办公楼。(后在九二一地震中倒坍,谁计算的R.C.结构已记不得。)在这工作之前,尚有一个小插曲。上班后不久,一天王先生要我在东吴大学后面山上一块坡地为他刚过世的王宠惠先生规划墓园。坡地不大,整地后只能有一小块平台。我的设计也只能很简单地在平台两边各留两片一砖半厚砖墙,墙间即为出入口,平台前面向外面临坡口处建一护栏,平台后面贴山处即为墓穴。我原期望王先生会加以修改此设计,谁知他看后却说这样即好。画好施工图发包后时值春假我去了南部,回程时在报上却赫然见载王宠惠先生的墓坍方了!看后如五雷轰顶,心想第一份差事就样丢去。后来还是硬着头皮去上班探个究竟。结果发现是包工程者偷工减料,在我原设计为石块的坡前档土墙做了手脚,仅将土夯成斜坡后在上面贴了石片,这样当然在大雨下崩坍。王先生在巡视工地时指着监工严厉指责,那是我所看到他的仅有一次发怒。我当然是官复原职,继续做下去,不过心理感激了王先生的信任。 在我之后被雇用的第二人是学妹林和珠。好像她母亲是日本人,工作不久后即因出嫁去了日本。事务所在中华路仅约半年,然后迁去怀宁街六号。同时加入工作的有学长潘有光及金石开,一年后又加入学弟谢伟,另加管事务及写施工说明及契约的胡先生以及文书许小姐。事务所终於有了一个最基本的团队。在去东海大学前我在怀宁街又呆了两年,其间经手绘图及部份设计的有丰原的太平塑木工厂、教育部、中央银行青潭仓、信义路二段号办公大楼,以及龟山之台北监狱。(注二) 怀宁街事务所内部的隔间是以木框嵌整片3’×6’石棉板(漆成橙红色)隔成,没有门。我们三或四人绘图员的工作室是靠外光线最亮处。王先生的图桌在里面,间接采光。在走道与他隔间之间有一上放置一些书刊的长条矮柜。柜子用多层广漆漆成红黑二色,极为漂亮,使得整个事务所都亮丽了起来。那时王先生来台已多年,认识了一些老工匠,包括漆匠师傅。有一次他对我说,一个房子的预算再怎么不够,只要在各处尊节,然后集中用好材料于一处,就会发生效果。譬如说在进门大厅处用石板铺地(那时在台湾几乎没有细石材),就会使人感到房子的尊贵。记不得我们曾否有过石板铺地的例子,但这漆柜精艳无比,确使来访事务所的人印象深刻。 对于一般委托案(如前述各案),王先生是由我们先做设计,他加以指点批评后修改即可。这些案件多是为事务所的营收所接。而我们几人都是成大毕业,在校时鼓吹现代建筑不遗余力,与王先生之绝不顺从官方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来供应仿古建筑的原则一致。(虽然他以后在国父纪念馆一案上遇到了麻烦。)所以我们依功能需要的设计只要大致可以他就放行。而他的修改则多半是针对立面、门窗样式与比例,以及材料与颜色,以收点睛之效。 遇到他认为较重要的委托(我在时有台大的大礼堂─后来未建─以及学生活动中心)以及可以发挥的私人住宅及俱乐部等案,王先生则亲自规划设计,其过程值得一述。 他先在他桌上的图板钉上一张约是A1尺寸的重磅水彩用纸。那种纸在台湾当时任何文具店都不可能买到,显然是托人从外带进的。穿着笔挺的西装,他用HB铅笔藉尺规先订下柱的位置。柱的开间通常是以英尺计,而常以2尺x2尺为平面尺度单元。然后思索着一步一步用铅笔画出墙壁来区隔空间。其间若有不妥,则用橡皮擦去再试一次。全部隔好后用鸭嘴笔上墨。这种逐步推导、干净俐落一次完成平面的手法,与我从前在成大时所见金长铭老师的改图方式完全相反。后者是用粗柔的6B铅笔在透明描图纸上涂改,不满意时再加一层纸继续。那是一种试误(tryanderror)法。王先生则是冷静地、似以操作手术刀的精细来切割空间。 然后他画立面图。在立面图上他很细心地尽量表达材料纹理,空心砖是一块一块地画出来。最后他常以正立面为基础而延伸画出一点透视。在学校时我们通常以两点透视为正宗,因为这样较符视野之现实。画一点透视太简单,常被看为不会画二点透视之替代。但来王先生事务所后,才发觉一点透视之好处。它是堂堂正正而大方,最要紧的是它不扭曲开间、梁柱,以及门窗的比例,而这正是他最看重的。总之,从完成的正立面及一点透视中可以看出建物完成后的真正感觉。他是将此正立面——透视图同时作为自己分析之用兼作对业主之表达。 在正立面图上,他不仅尽量表达材料纹理,也上颜色,使其与日后建物所用颜色尽量相近。这倒不难,因为他的建物大多是白墙或用白面砖(二顶挂)及灰色柱梁,仅是在进口处大门或其它重要部位用色。而图纸是白的,只需在相关部位着色即行。关于颜色,以下再叙。图画好后他会在左下角编一图号。而这图号字码也是先用铅笔设计勾划后再用墨笔嘴填黑,字体近于现在电脑上显示的TimesNewRoman体,非常正派挺秀。最后,他可能从画报杂志上剪下个人像来贴在这正立面透视图上适当位置,不仅给了比例,也使得图面突然活了起来,好像所设计的空间一下子就与现实世界相接,效果非常特殊。我相信这是王先生的独创,自他从年为Interiors杂志所提出的TheAtriumTownHouse中呈现后,他一定非常喜欢这个效果。 但王先生绝不是一个纸上设计建筑师。相反地,他是最着重实践经验的人。对我画的大样他常会评论:「这个太贵」、「这个比较好施工」。有一次对我画的一个预铸水泥块,他问「你用双手搬不搬得动?」他提过在哈佛设计学院读书时,曾帮同班同学PhilipJohnson在剑桥盖过后者的自用小宅,(注三)工作包括砌砖、木工、油漆。无疑他从中学到了营造。有一次,在一个仓库里,他对我指着一个铁楼梯说:「虽然看似很陡,你走走看,很舒服。」要我记住踏步的高深尺寸。而我当时只知道按照日本出的建筑标准图集,依不同楼梯角度来定踏步的高深比例。 王先生对颜色有一定手法。通常他设计的房子以白色或灰白为主调,而在部分如大门或者後面大厅正壁上用上极重的颜色,至今在我眼前还显出图面上福乐奶品公司办公平楼进门处上方的金磨赛克横板,上面的字是红及黑色,富丽堂皇极了。他对金色有喜好,但不常用。有一次他在建国南路自宅的客厅中正面白壁上随意贴了一些金箔,煞是好看。一天他临时要我陪他搭公车去基隆(还是苏澳?)火力发电厂。通常这些厂内都是幽暗阴沉,可是我进厂后眼睛一亮,原来厂内机器经他建议后全部涂成一种孔雀毛的那种蓝绿色,涣然一新,表达了一个现代化机房。颜色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他对颜色的差异极敏感。有一次,在看过我为某设计上的颜色後,他再望望我,问到:「你是不是有点色盲?」几年前,曾有人听我提过此事后去向王先生求证,他矢口否认,说绝不可能。确实,王先生虽然看似严肃,绝不会駡人─他似乎以为我记得此事,是因为感到挨了駡而有不快。事实刚好相反,我是以感恩的心记得这次评语,因为从此以后,才知道颜色的差异是多么细致精微。红色里不止是有几种红,而是有几十种甚至於上百种可辨识的(而我以前未能辨识的)红;蓝色、黄色、绿色也是一样。 王先生对梁柱构成的开间以及门窗之权衡比例的重视一如MiesvanderRohe。不过後者比例之特点是宽宏,而王的比例特点是直长挺拔,承继了中国门扇窗精神。国父纪念馆进口的清水梁柱之三开间的比例尚较雅典卫城上Parthenon庙的柱范比例更耐看;在台湾巡视至年代间之建筑时大约可从门窗比例看出是来自大洪事务所。 矩形当然只有比例可言。对于可以不是矩形的门窗开孔、水池、花坛的型式,他常思考如何创新而不落俗套。在公用建筑大门外,总是需要一个圆形的草地或水池,以便车辆流转。记得有一次他在窗前往外往外看了许久,回首跟我说:「注意到没有,砚台上磨墨的结果,是非圆非方,也不是椭圆,也许可以拿来代替圆形来做回车道」。不久後果然见他在某个设计图上画了这样形状的一个回车道,但不知道以后是否实现。倒是后来从图上看到他在天母陈宅进入大门后的一个门洞(萧梅《王大闳作品集》p.)以及我去过的石牌弘英别墅中他自宅里餐厅后面的门洞以及起居室的窗孔(徐明松《永恒的建筑诗人王大闳》p.,p.)都是这个形状。虽然人们都称此为团扇形,(其实,中国团扇通常是一边较大,另一边较小。)我确信,此形原出于他从砚台中看到。 当时台湾物质条件低劣,建材贫乏。门上的黄铜把手是简单的横式,锁钥另开。现在通用的铝合金把手与锁钥合一的所谓「喇叭锁」在当时似尚未出现。有一天见到王先生带了这样一个喇叭锁样品进来说:「台湾终于有了起码像样的门把手了」。然後他提起他在欧洲某展览会上看到的一个门把手,设计成为一个伸出的金属人手。宾客握此手一扭转而进门,颇具创意。既然他提到欧洲,那就是他20年前年青时的事了,这样的一个门把手居然记得,可见他对设计创意的留心。而再五十年,我这平常以健忘知名于亲友间的人,也忽然记起此事,想来也感到奇怪。 五十年前在大洪事务内所见所闻的点点滴滴,大约只能爬疏我尘封的回忆之室到此。不过反过来想,当时那些是没有见到或听到但或有意义的,也值得在此一提。 首先是从来没有听过王先生提过什么设计理论或是什么主义,或是对中国建筑的现代化路途表达任何意见。只有一次听到他说过:「好就是好嘛!有什么理论?」我想这最能代表他以品味来设计的根本主张。另有一次,他对我说:「好在现在还有Mies压一压」,意思是当时国际上建筑设计已有多元趋向,不够格调的商业建筑到处出现,但是Mies的精简尚有制约之效。这是年代的末期,我不知后来他对後现代主义建筑兴起的反应,何况PhilipJohnson也开头有份(注四)。 他亦未曾提过他当时与国际建筑界有何联系,这当然是我们不足为他告知的对象,亦是因为他生性淡泊,不屑渲染。贝聿铭先生於年访台,当时我还是学生,曾有一次眼前他与王先生互动亲切(注五),似乎他们相互敬重而一直有连系。至於Gropius还记得王先生一事,也是我到美国后有幸见到前者方知(注六)。 他更未曾提过他以建筑作为一项工作之外的喜好以及他的平日生活趣味,这当然是也是我们年青人一代的环境经验,孤陋寡闻,不足为语。他曾经将他用过的一些78rpm的古典音乐唱片在报上登过一次售让小广告後放在事务所内,引来一批音乐爱好者看片。前述的矮柜上曾经放过一些当时台湾难得见到的一些法国19世纪画派的画册。(他曾说,这些法国画派要连续一起来看,才有意思。)从这些我知道了他对音乐美术的嗜好,但当时完全不知道他对文学方面的兴趣,这要在以後从(萧梅编)《王大闳作品集》里刊载的他部份着作与翻译(多出於年以後)方可见到。当然《杜连魁》一书不仅代表了他的文学能力,更是可从其中的描述,最能全面地说明了他对欧美上层社会生活的熟谙与王尔德式的美学。 他并未提及当时他与台湾文艺界的往来。时代是台湾包括「现代诗」在内的新诗之茁壮年代,也是「五月画会」与「东方画会」的年青现代主义画家们撼动绘画界与社会的年代。当时在文学界与绘画界之间尚有人(如余光中先生)居中来往、沟通讯息,但他们似乎不了解正在发芽的台湾现代建筑,更因此未知王大闳先生(注七)。而王先生也似乎未曾看到他们。 王大闳先生在西元五十年代以后,结合了两个要素而在台湾创造了一个属於他自己的建筑风格。一是西方的现代机能主义(特别是其中属於Mies的精简取向);另一是中西文化里的菁英品味。前者是横的移植,也是当时建筑界年青一代努力宣扬的主张。它是可以学习的,也必然会成功,因为它符合了时代与社会(包括市场)的需要。后者是纵的传承,只有少数人士,因为家世背景与机遇而有缘吸纳了中西文化的精粹。而王先生是此菁英中唯二人士─其它一位即是贝聿铭先生─能将此中品味溶入于建筑,作了对社会的文化贡献,而不限于仅为个人消费。 与贝相较,王先生毋宁是更具有一种贵族气质的,他不再乎社会世俗对他的建筑作品或是个人生活的评价。他的兴趣,尤其是在晚年,似乎是超越尘世之上而属于太空之境的。在世上,他所居住的地方,就是他心安之处。来台近六十年后竟也不曾回去再访一次欧洲或美国!他有一个完整的内心世界。他不仅是台湾也是全球华人中最后一位贵族。 这些都说明了为何他在台湾的建筑发展有限。他的恬淡矜持,不宣扬、不着述立论、更不拜求关说,加上官方对建筑文化的不解与漠视,使得他在台湾竟无一件他想要的大型建筑留存。知名的国父纪念馆更不是他自认的代表作,而是一个妥协的结果,最后几乎是以讽刺的手法展现。(似乎他在清楚地说:「好,你们要中式屋顶,我就给你们一个最大的!」)他的那些优异的住宅作品,多已被不动产市场吞噬,仅有行家能藉图面与照片神游其中来欣赏其艺术造境。他是建筑师的建筑师,仅为圈内人所知。 如要大鸿在雪泥上留下爪痕并加以冻结、让世人认识到台湾也有建筑艺术精品的办法其实不难。目前大陆中国不惜代价在北京兴建了一批使举世侧目的建筑,藉以宣告中国的现代化。这些建物无关中华文化,亦无一为华人所设计。这倒供给了台湾一个便宜而鲜明的对照机会。如果台湾官方或民间能将王先生他唯一关心的登陆月球纪念碑以什么名号在台建造,那将会告诉世人中西美学的结晶体可以美到什么程度。MiesvanderRohe年在西班牙巴萨隆纳世博会的德国馆现己被巴市重建,藉以提醒此馆的影响力及历史价值。我们更应将王先生建国南路的住宅择地复制重建,向全球昭示中华文化如何在台湾与现代接轨。 注一那时一般人对建筑师和营造厂老板也是分不清,能了解建筑师职在设计的就算不错。不过人们提到建筑师时会说:「他画一张图就可以卖多少钱哟!」(建筑师在广东话中被称为「画则师」,在上海话中则被称为「打样师」)。 注二在设计后者时,王先生提到过在欧洲曾有人将监狱之各排牢房安排为放射状,以便在核心处一人即可监视全狱。出国后读书发现此人竟是人道哲学家而以功效主义知名之边泌(J.Bentham)。记得龟山监狱近完工时包商曾要求将他关一夜,以赎建狱之罪。我等设计与绘图人闻後不禁惘然。 注三此时PhilipJohnson己于十多年前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创设了建筑及设计部门,介绍了「国际样式」建筑给美国。也是他协助了MiesvanduRohe及MarcelBreuer移民美国。他去哈佛设计学院回锅当学生时,早已誉满欧美,这说明了当时专业学院里Master学位之意义。王先生帮他在剑桥所造的住宅记得是在AshStreet。我曾去看过,只是为高墙(木墙)所阻,不见其内。王先生曾告诉我:因为美国住宅之间都是矮栏杆相隔,互相看透庭院,此宅建好后,左右邻居还去向PhilipJohnson问是什么地方得罪了他,才用此高墙隔阻。此宅(?)与王先生的AtriumTownHouse(-45)以及王先生在建国南路自宅()均赋予外墙同一功能:隔离外界而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内部庭院空间。 注四PhilipJohnson在纽约设计有ATT大楼(现为Sony大厦)。他在楼顶加了一山墙且有一巴洛克式装饰性开口,可视为从现代主义转向历史主义手法之滥觞。此建物完成于年,但设计图发表于70年代中期。我当时在美国匹次堡Carnegie-Mellon大学为讲师,犹记得隔院的建筑系教师们见到此图后所表现的惊讶与迷惘。一叶知秋,他们当时从此案已知一个设计的新风尚世代即将开始。 注五记不得是在台南成功大学,还是在台北某处,贝在演讲完还在台上时,王先生从外走进,手拿一小布袋送给贝,说你会欢喜的。贝闻了一下,极为高兴说:「大闳,太好了!你真想得周到。」后来得知,那是袋桂花子。 注六时值前后,在哈佛大学的爱默生楼(EmersonHall,当时设计学院所在二楼之一)里一个派对中,Gropius也大驾光临,我乃趋前攀谈,自我介绍曾在他廿年前的学生Da-hongWang事务所工作过。本想他未必会记得王,未料他立即反应:Heisverytalented!春Gropius去世,当时越战中学生反抗运动高潮未过,校园动乱。哈佛校刊Crimson报导Gropius遗孀力排众议,仍按Gropius生前遗愿大事举行庆丧会。此二事我于年夏回台时,曾向王先生禀报。他未置评,也未提到现在已刊载的Gropius於年寄给他的手抄诗。 注七不过我在成大学生时代,曾有外来画家何铁华先生来校演讲,他因到过王先生济南路自宅而大为惊叹。何的现代画在台北遭受报上的挞伐与讥讽,后即离台,似乎未在台湾绘画界留下痕迹。 封面图片来源: 投稿/contribution xiangchoujingji.北京白癜风防治医院北京治白癜风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wyszentea.com/lscp/1215775.html |
邀稿华昌宜在王大闳身边的所见所闻
发布时间:2017-6-4 9:31:38 点击数: 次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2015读书计划一建筑学与建筑理论
- 下一篇文章: 装修陷阱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