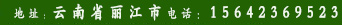|
我时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来思考问题,很多烦难问题就变得易解。 ——王小波 我的文学殿堂 梁路峰(江西遂川) 年金秋时节,我怀着期盼已久的心情,来到了北京,来到了心驰神往的鲁迅文学院。由于工作原因,我推迟了一个星期赶到鲁迅学院报到,没有参加开学典礼,未能与同学们第一次见面合影,留下了许多遗憾。 在鲁院,我见到了诸多令我仰慕的作家、评论家、诗人,倾听了许多知名大家的讲座,与著名作家、评论家进行文学对话,参加了陕军作家梯队作品研讨会,聆听了文学导师的零距离讲课。每一节课都是对我的心灵进行文学的洗礼,通过学习、互动交流,作品修改、评点,以及鲁院老师的悉心指导,使我终生受益,得益丰厚。 鲁院的早晨,院子里满是红枫树林,曲径小道已经铺满了飘落的红叶,三三两两的同学沿着院子的小路转悠起来,个个意气风发,脚下有使不完的劲,我和庆玉兄散漫着脚步,谈笑风生,用心地、细细倾听着红叶落地的声音,用大山走出来的双脚丈量着鲁院的每一寸土地。 早晨的院子,伴随着东边太阳的照射,我感到全身的热量开始沸腾,该吃早餐了,该上课了,一串响亮的上课铃声中,我们争相走进了课堂。 每天晚上回到宿舍,我要重温白天导师的讲课,把笔记本三番五次地翻阅,把没有记清的笔记补上,把导师在课堂上所讲的经典故事重新温习一遍,我感觉,一股创作的冲动,在心里沸腾。 深夜,躺在鲁院宿舍的床上,我不断在做着奇妙的梦,明天是哪位老师讲课,有时半夜起床打开灯,查看课程安排,睡下后,心想,明天的课会有什么收获?睡下了,梦里总是问:我是在北京吗?我是在鲁迅文学院吗?我总是问自已,可也在回答自已:是的,一刻钟也不能浪费! 于是,我常常挑灯夜战,在鲁院两个多月,创作了一篇报告文学、一篇纪实文学、三篇小小说,用激情书写了在鲁院的时光,用朝拜的诚心,珍惜着在鲁院的每时每刻。 在鲁院学习70天,与鲁院的院领导、班主任和诸多老师成为亲密的朋友,与和蔼可亲的导师面对面交流,与全国各地的同学们讨论作品,探讨文学,品头论足,他们的笑容,语重心长的教导,成为我文学人生中最珍贵的财富。 作为48名学员中年龄最大的一名学员,我深深感到追赶前行的压力,带着惶恐不安,埋头听讲,暗地里树立知难而进的信心,与同学们共度美好的鲁院时光。 在鲁院学习的日子里,让我感动的是每一个教授、作家一言一词的演讲和教导,每一字句的敦敦诱导,让我铭心刻骨,激励我在文学创作路上不断创新前行。 在鲁院,李敬泽、施战军、李师东、麦家、周大新、李洱、顾建平等一批著名作家的授课,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记忆。李一鸣副院长学养深厚,讲课旁征博引,妙语连珠,让我久久难忘。李院长说,要写好文学作品,首先要把握当下文学存在的问题,了解作家创作存在的心态。心态方面,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如王安忆所说的“一天天地写,一行行地写”,坚持而勤奋;一种是认为技巧很关键,以技巧取胜。李院长对一些文本进行了似乎褒扬性的分析后指出,上述两者都重要,但相比起来,“道”最重要。何为“道”呢?李院长说,人文情怀、哲学素养等就是“道”。 在鲁院,让我感到严迎春老师的关怀温柔敦厚,每一次的对话和询问,让我温故而知新,她的慈爱,在我脑子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我生活、工作中永远难忘的记忆。严老师与鲁23班全体同学对我这个特殊学员的关心关怀,植入我永恒的美好记忆中。 鲁院70天的研修,使我找到了文学创作的感觉,走出了公安文学创作多年的原始困惑,鲁院为我搭建了一个天大地宽的文学创作、吸吮知识的平台,让我在今后的文学创作中不断创新,精益求精,使我进入一个崭新的文学创作天地。 难忘在鲁院的日日夜夜,难忘鲁院给予我文学创作的新鲜源泉和血液,难忘鲁院老师的深情教诲,难忘鲁院同学们的深厚感情。 忍冬 杨莹(江苏句容) 金银花有一个很诗意的别名,叫忍冬。听上去,有点沧桑的意味,默念起来,却又充满了人生的况味。阴冷而漫长的冬天,很多草木都变得无精打采,金银花却将根深扎大地,隐忍地守在那里,哪里也不去。它的使命仿佛就是等待春天。当一阵春风轻轻掠过,一场春雨细细洒落,漫山的草儿返青变绿,熬过一季严寒的金银花,开始了不动声色地微笑,吐呐之间任由春光染绿裙裾,牵藤附蔓之际,蕴藏着势不可挡的力量。 忍冬是一种藤本植物,一钻出泥土,就蔓生出烟翠的藤叶,依附于低矮的灌木上丛间。细小的白色花蕾,一如帷幕中初眠的稚童,带着清浅的笑。盛开之时,一蔟簇洁白的小花在椭圆形细碎的花瓣中伸出小小的心蕊,微敛如美人心内的羞怯,散发出若有若无的清香。慢慢地,花朵转为淡黄,嫩黄的瓣儿呈半透明状,简单、单薄,却美得让人驻足,仿佛美人手里紧攥的素帕儿,时而淡黄,时而绢白,一朵一朵,在指间飞扬着,空灵又婉约。清风徐来,那些帕儿在风中纠缠,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细微又清脆。 暮春的田野,尤其是有青蛙呱呱、蚱蜢蹦跳的田边地头林间,总会有它们黄白清新的身影。夏日昭昭,金银花并不疯长,很有主见地在风中摇曳着它们细溜溜的腰,寂寞地依附在老藤叶间,时不时挂住路人的裤脚,或拉住衣襟,以一片叶的脉络,一朵花的嫩蕊招惹人们眼底深处的眷念。那妖娆的绿叶长藤青蔓,那幽幽的香气犹如入画的一景,画面清新柔美,恰如其分地寓意着金银花的花语——全心全意把爱奉献给你,暗合着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愫,那种轻柔的、微醺的、细细长长的情愫。 散步在春夏交替的季节里,怀旧的情绪水雾般弥漫上来。记忆中,住在山脚下的女人们,一到金银花盛开的时候,就会挎个竹篮,三三两两地上山采摘。进了山,人影纷纷散了,等到午蝉拼了命似的在林间喧嚣,不知是谁先吆喝了一声,女人相继出来了。金银花是农家常备的药草,采摘却自有一番讲究。通常要等到上午九点,阳光蒸发了露水之后上山,采摘的时候专拣花蕾上部膨大又没完全开放,泛着青白色泽,香气浓郁的那种。这种花很嫩,民间俗称大白针,因为它即将开放,必须轻采轻放,回家得用竹箔或草席摊薄了晒干。据说,四五斤鲜花才能晒一斤花干,不少上了年纪的老人也去山上采摘,他们除了饮用保健外,还一篮一篮的运到供销社卖钱。 ?金银花自古被誉为清热解毒的良药。它在药物志上,一直享有“药铺小神仙”之誉,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卫生部多次对金银花进行了化学分析,发现它含有多种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和化学成分,同时含有多种对人体有利的活性酶物质,具有抗衰老,防癌变的神奇作用。 金银花的花期很长,能从四月盛开到九月,那青青的忍冬藤,也是入药的良方。青青翠竹,郁郁黄花。春去秋来,看似一季的繁盛已经孕育着下一季的凋零。然而,金银花却是无悔的,它平凡地盛开在山谷之间,雅致地绽放在春夏枝头,仿佛所有的美好只为自己。金银花就这么默默地经过夏,走过秋,忍受寒霜冷雪,在绿色的藤蔓之间,晒着日光,听着风,萌着新芽,等待来年的花开。 小镇记忆 彭建群(四川峨眉山) 儿时的许多记忆逐渐淡忘乃至消失,但故乡江口镇那由吊脚楼、岷江河、石板街构成的江南水乡古镇风貌,却依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那遥远记忆中的古镇,还是那么清晰…… 在我最初的记忆里,它是那么热闹美丽。镇外有府河与南河两江汇合,由于府河的水青绿,人们叫青龙江,南河的水浑黄,人们叫它黄龙江。两江汇入岷江流向了长江。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带着我到处去赶场,去得最多的就是江口镇,我的家离古镇10多里路,那时没有公交车,只能步行,对幼小的我来说,路途比较遥远。每逢古镇赶场,我总是乐于步行去江口。 到了镇上,我帮父亲卖红薯或玉米,守在箩筐前,觉得很不好意思,有人问价,我还没开口,脸就先红了。最后,自己报价的声音低得像蚊子声,父亲走上前来,大声地和买主讨价,这时,我就偷偷跑去看热闹了。 古街上有豆腐坊、榨油坊、铁匠铺、竹篾铺,还有供销社,更多的是茶铺、小吃店、小吃摊。茶铺里就更热闹了,闲聊打牌的人、赶场歇息的人、喝酒吹牛的人,花一毛钱或两毛钱就可以一杯茶泡一天。老板泡茶用的是长嘴铜壶,在一个大的蜂窝煤炉灶上,同时烧了十多个长嘴铜壶,哪壶开了就提哪壶给客人泡茶加水。看着老板里外忙碌,听着他大声吆喝,真有趣。有时口渴了,又不愿意出钱泡茶,我就会走到一个看起来很和善的老爷爷傍边,低声要茶水喝,老爷爷总是很热情地把盖碗茶端给我喝个够。 古镇有几家铁匠铺,一到赶场天,铁匠们赤裸着上身,挥动着铁锤,砸得砧铁火花四溅,伴着“叮当”的钢鸣和铁匠们的吼声,如歌的乡音和打铁的声音如交响乐般混合演奏,在古镇上空回旋。 古镇有很多家竹篾铺,背篼、箩筐、蒸笼等摆满一条长长的街。竹制品因为无毒而且价廉,深受大家喜爱,那时还很少能见到塑料制品。店主们一边卖一边还在编,那粗糙干裂的手在不停地舞动着,他们是那样认真而专注。 古镇还有卖手编草帽、草鞋等麦杆编制的用品,农村的大姑大嫂、小姑娘、老婆婆们在农闲时就把收割后的麦杆晒干,选最好的麦杆编织草帽、草鞋等用品,甚至男人们也加入了编织的行列。我小时候也帮妈妈编织过草辫子,妈妈将我编织的草辫子做成草帽拿到古镇去卖,换点钱买盐、针线等生活用品。有时候,妈妈将我们编织的草辫直接卖给别人,别人拿去做成其他用品。 古镇有很多小吃,每次父亲卖完东西,都会给我买好吃的。到了下午,赶场的人们渐渐散去了,我还依依不舍地留在街上,虽然身上没有一分钱,但我在古镇的电影院隔着门缝,还可以偷偷看一场电影。我一生中看的第一场电影就是在古镇的电影院门缝里隐隐约约偷看到的。 我14岁开始在彭山县读高中,住校,那时没通公共汽车,每个星期六下午放学回家一次,只能步行30里路回家,每次经过岷江渡口,看着卖船票的姐姐,就觉得读书实在是太苦了,如果能有一份卖船票的工作,哪怕一个月只有二十元钱的工资也好啊。 近日,我特意回故乡去寻找记忆中的古镇江口。这里依然山清水秀,吊脚楼房伸入江面,茶房酒肆比比皆是。现在的江口镇是现代建筑与古镇风貌混合在一起,古韵与时尚在江口镇共存。走在故乡的小镇上,我在心里寻找往昔的记忆……这时,小巷深处传来小贩叫卖时拉长的乡音,悠扬而亲切。在汉崖墓博物馆、桥楼子、横街子一带,还保留着川南江边码头小镇的古朴风味,让江口的古老与神秘坚强地留存至今。 故乡的小镇,我儿时的乐园,它以一种让我无法忘怀的方式连接着我,似乎遥远,而又似乎近在身边…… 记忆中的供销社 罗昭伦(重庆万盛) 从家乡洗布河上搭着水泥板的桥面走过,不到十分钟,就是我们村的村委会。村委会的旁边是村供销社。这座土夯石垒、白墙黑瓦的两层楼房,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建的。周围的建筑都是木瓦房,明显不如它气派。两扇漆着天蓝色油漆的木质大门,在村民低矮的土坯房映衬下,显得格外雄伟壮观。 记得在我上初中的时候,供销社翻新过一次。经过翻修后的供销社,房子高大了,院墙结实了,墙顶上安装了玻璃碎片,供销社营业厅窗明几净,柜台都是标准化的玻璃货架。营业员大都是从城里来的知识青年,穿得很洋气,也很干净。日用百货发出好闻的气息,不管是买不买东西,人们都愿意经常去光顾。上学的路上,我常去那里,看着那些牌子上画得水果,有点望梅止渴的味道。尤其是夏天,那画上的西瓜给人一种清凉感,是我最爱看的画。我最常去的柜台,就是那个卖酱油、醋和糖果的柜台。那些糖果,光是看着,心里就有一种满足感。如果母亲让我去打酱油什么的,我很乐意去,因为酱油八分钱一斤,打完酱油以后,手里往往会剩下一两分的零钱,母亲会允许我们买一两块水果糖。 那时候,有一种我们最喜欢的铅笔,就是现在的中华绘图铅笔,绿色的外皮,上面有一些深绿的竹叶图案。我那时都叫它“一毛一的铅笔”,因为它的价格是一角一分钱,可以买普通的四支铅笔。这种铅笔的铅芯很硬,不易折断,而且写在纸上颜色很浅,显得字迹很干净。后来才明白了,这种铅笔的芯是2H的,颜色浅,硬度高。有一年期末考试前,听几个同学说要买这种铅笔写答卷,回家求母亲给买一支,母亲很痛快地答应了。下午放学后,拿着一角一分钱,跟着同学去商店。那天正好商店盘货,早早地关了门。我望着弹簧木门外紧锁的折叠铁门,心里无限惆怅。幸好,一个同学说,他爸爸就在供销社上班。我转忧为喜,和同学从后门进了供销社,终于如愿以偿。 供销社虽小,但在当时是全大队新闻传播的中心。冬季里没活干的人、老年人、邮电局送信的,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供销社烤火,帮助烧炉子、闲聊天,能把各生产队乃至公社的大事小事捋个遍,有时上溯到古今中外,下涉某户某人。当时,村民们家里没什么钱,但家家都养鸡,到供销社买东西不用付钱,直接拿鸡蛋换。一个鸡蛋可以打一瓶酱油,换三盒火柴,称八两盐巴,换三根香烟…… 随着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越来越多的人做起了生意。取而代之的是个体户,民营超市。有人开了专卖店、电器城,商品款式越来越多越来越新,琳琅满目让人眼花缭乱。供销社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渐行渐远,只留下一串串美好的回忆。 前次回乡,听老人们说,而今到处又可以见到供销社人的身影,他们依然战斗在服务“三农”的第一线,帮助农户成立专业合作社,开建电商平台,在网上,就可以将本地无公害、纯天然的产品销往更为广阔的市场! 闲语 付廷江(四川会理) 就算心绪再乱,也要有一颗纯真善良的心,不要染上所谓的江湖气息。善良不是做给谁看,是自己对得起自己的心,害人之心不可有,最起码不能做个心眼坏的人。 去爱你想爱的人,去写你爱写的诗。你不需要成为一个传奇,但你一定要足够努力,让世界留下你来过的痕迹。不一定每天都要欢歌笑语,但一定不要愁眉苦脸;不一定你爱的那个人就一定要爱你,但一定要用尽全力;不一定夜夜辗转就是坏事,也许就有最好的诗句在最美的梦里和你不期而遇。不要惧怕世俗,不要囿于压力,在善良的前提下做最真的自己。在朝阳中跑步,在下午的暖阳里喝茶,在傍晚的路灯下数星星。有时候,约上三五好友,喝一点小酒,在酒酣之际,别让思念变成泪水,和雨一起滴。 心里藏着的感情,因为太美,才不愿有任何的变数,哪怕就这样凝望你。若不说破,我便可以永远爱你,保持一个美好的幻想,或许可以陪一辈子。爱恋,是最纯真。得与不得,倒是次要,我爱你,是单纯的想你好。当然要是你的每一个笑容都有我的参与,那自然更好。可是在没有把握的前提下,我宁愿以局外人的身份,参与你人生的很多片段,我们可以为一些事情一起抱怨一起笑。然后,就由天意,或许因为你,离开也要用尽全部勇气。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再遇到第二个你,把这种遗憾只好埋在心底。纵然有你的地方就是故乡,可你的不在意,还是会平添我的忧伤,所以,不如归去。 其实你不知道,在这里的每一首诗、每一篇文,都是因为你。让我怅惘和开怀,伤心和窃喜,都是你的不经意的一句话,一个动作或眼神。怪你过分美丽,今生注定无缘,我们来生再相遇。他们不懂阁楼上的人的抽噎,是伤心还是欢喜。了却这一段错误的时光不提,最开怀,最俗的话语:在最美好的年纪遇到最美的你。只是此时,亦是我最不堪的年纪,哪里有什么来奢求照顾你。 朔风吹不走眼泪,树叶落不完叹息,梦醒时分的妩媚。总是你,让我埋下头喝完了杯里的岁月,诉说着遇到你,好开心,好幸运。 捉迷藏 李火生(广东佛山) 人到了一定年纪,反而对过往的很多事记忆犹新,最近,我常忆起儿时在乡下捉迷藏的情景。 明月高悬的夏夜,清风送来阵阵荷香和蛙鸣,龙眼树上的鸣蝉也时缓时骤,蟋蟀欢快地弹奏着悠扬的小曲……一会儿,孩子们的喧闹声就压倒了这些声音,成了寂静的夏夜主旋律。一群小家伙正在生产队里打谷场周围高高的稻草垛前,挥动着小手,激烈地进行着“剪刀石头布”。激战之后,游戏便开始了。 小伙伴陈胜被人蒙上眼睛,拉着转了好几圈,然后摇摇晃晃地站在原地等待着“吆鹩哥得”(开始找人的口令)的口令,其余的孩子四处散开,钻入稻草堆里藏起来。 我早在白天就做好了藏身的“地道”:把几个连接的稻草堆全部挖通,通道弯弯曲曲的,一直挖到草垛的半腰。待进入“地道”后,我便把通道堵死,佯装通道到此已不再向前延伸的假象。然后,我就爬上草垛半腰的掩体里,只露出一个瞭望孔,偷偷看着陈胜到处瞎翻找人的狼狈相,捂着嘴巴偷笑。陈胜找不到人,就耍起计谋来:哈哈,山狗崽,我看见你了,别再躲了,快出来吧!陈胜咋咋呼呼地嚷着,你再不出来,我就要用竹竿捅你的小屁股了。山狗崽不知是计,急忙从草垛里钻出来说,别捅別捅,我出来了。陈胜计谋得逞,捂着肚子笑得前俯后仰。藏在草垛里的伙伴们听见笑声,都从藏身的地方钻了出来,一齐笑了起来。打谷场上的笑声,吓得宿在树上的鸟雀都扑棱扑棱地飞了起来。 换了几趟人,都没有一个人发现我。看着看着,我竟然在掩体里睡着了。 伙伴们找不到我,就回家睡觉去了。母亲在家里左等右等,不见我回家,就去找邻居的伙伴询问,然后大家出动寻找,找了老半天,也没找到。后来,我被伙伴们的叫喊声惊醒,才爬了出来,母亲臭骂了我一顿,然后揪着我的耳朵回家睡觉去了。 还有一次,我钻进“地道”后,就悄悄地从后面的出口溜走,回家睡大觉去了。伙伴们一直到散场,也找不到我,于是吸取上次的教训,到我家告诉母亲。母亲对伙伴们说,狗娃一个晚上都在家里睡觉,哪也没去呀,咋会不见了呢?伙伴们看着睡眼惺忪地从家里走出来的我,面面相觑,哭笑不得。 现在,我虽已过花甲之年,但还是喜欢和两岁的孙子玩捉迷藏,但可惜的是,现在已经没有大片大片的农田,没有打谷场,也没有稻草垛……面对林立的高楼大厦和纵横交错的柏油马路,我们只能躲在窗帘、门角、蚊帐后面玩了。要是时光能够倒流,回到儿时的乡下,再玩一次捉迷藏,那该多好呀。 编辑:魏文红 点击进入大凉山 优品汇网上商城 北京哪里治白癜风好白斑疯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wyszentea.com/lscp/1215144.html |
美文点进来好文章让你一次性看个够
发布时间:2017-3-17 16:37:20 点击数: 次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绿色生活家中花草您知道哪些
- 下一篇文章: 家长必须知道的quot第十名现象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