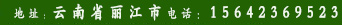|
小红门一关上的时候,就是永别的时候吗席慕容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再继续做的;有很多人,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再见到面的;于是,在你暂时放下先或者暂时转过身的时候,你心中所有的,只是明日又将重聚的希望,有时候甚至连这点希望也不会感觉到。因为,你以为日子既然这样一天一天地过来的,当然也应该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昨天、今天和明天应该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但是,就会有那么一次:在你一放手,一转身的那一刹那,有的事情就完全改变了。太阳落下去,而在它重新升起以前,有些人,就从此和你永诀了。 就像那天下午,我挥手离开那扇小红门时一样。小红门后面有个小院子,小院子后面有扇绿色的窗户。我走的时候,窗户是打开的,里面是外婆的卧室,外婆坐在床上,面对着窗户,面对着院子,面对着红门,是在大声地哭着的。 因为红门外面走远了的是她疼爱了二十年的外孙女,终于也要象别人一样出国留学了的外孙女。我不知道那时候外婆心里在想些什么,我只记得,在我把小红门从身后带上时,打开的窗户后面,外婆脸上的泪水正在不断地流下来。 而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外婆这样地激动,心里不免觉得很难过。尽管在告别前,祖孙二人如何地强颜欢笑,但在那一刹那来临的时候,平日那样坚强的外婆终于崩溃了。而我得羞耻地承认,在那时,我心中虽也满含着离别的痛苦,但能“出国”的兴奋仍然是存在着的。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使我流的泪没有老人家流的多,也才使我能在带上小红门以前,还能挥手向窗户后面笑一笑。 虽然我也两眼酸热地走出巷口,但是,在踏上公共汽车后,车子一发动,我吸一口气,又能去想一些别的事情了。而且,我想,反正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反正我们很快又会见面的。而且,我想,我走时,弟弟正站在外婆的身后,有弟弟在,外婆不会哭很久的。外婆真的没有哭很久,那个夏天以后又过了一个夏天,离第三个夏天还很远很远的时候。外婆就走了。 家里的人并没有告诉我这个消息。差不多过了一个月,大概正是十二月初旬左右,一个周末的下午,我照例去教华侨子弟学校。那天我到得比较早,学生们还没来,方桌上摆着一叠国内报纸的航空版,我就坐下来慢慢地翻着。好像就在第二张报纸的副刊上,看到一则短文.一瞥之下,最先看到的是外祖父的名字,我最初以为是说起他生前的事迹的,可是,再仔细一看标题,竟是史秉鳞先生写的:“敬挽乐景涛先生德配宝光濂公主。” 而我当时唯一的感觉就是手脚忽然间异常的冰冷,而我才明白,为什么分别的那一天,老人家是那样地激动了。难道她已经预感到,小红门一关上的时候,就是永别的时候吗?而这次,轮到我在一个异国的黄昏里,无限懊悔地放声大哭起来了。 一个人无论多大年龄上没有了父母,他都成了孤儿周国平一个人无论多大年龄上没有了父母,他都成了孤儿。他走入这个世界的门户,他走出这个世界的屏障,都随之塌陷了。父母在,他的来路是眉目清楚的,他的去路则被遮掩着。父母不在了,他的来路就变得模糊,他的去路反而敞开了。 我的这个感觉,是在父亲死后忽然产生的。我说忽然,因为父亲活着时,我丝毫没有意识到父亲的存在对于我有什么重要。从少年时代起,我和父亲的关系就有点疏远。那时候家里子女多,负担重,父亲心情不好,常发脾气。每逢这种情形,我就当他的面抄起一本书,头也不回地跨出家门,久久躲在外面看书,表示对他的抗议。后来我到北京上学,第一封家信洋洋洒洒数千言,对父亲的教育方法进行了全面批判。听说父亲看了后,只是笑一笑,对弟妹们说:“你们的哥哥是个理论家。” 年纪渐大,子女们也都成了人,父亲的脾气是愈来愈温和了。然而,每次去上海,我总是忙于会朋友,很少在家。就是在家,和父亲好像也没有话可说,仍然有一种疏远感。有一年他来北京,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他突然提议和我一起去游香山。我有点惶恐,怕一路上两人相对无言,彼此尴尬,就特意把一个小侄子也带了去。 我实在是个不孝之子,最近十余年里,只给家里写过一封信。那是在妻子怀孕以后,我知道父母一直盼我有个孩子,便把这件事当做好消息报告了他们。我在信中说,我和妻子都希望生个女儿。父亲立刻给我回了信,说无论生男生女,他都喜欢。他的信确实洋溢着欢喜之情,我心里明白,他也是在为好不容易收到我的信而高兴。谁能想到,仅仅几天之后,就接到了父亲的死讯。 父亲死得很突然。他身体一向很好,谁都断言他能长寿。那天早晨,他像往常一样提着菜篮子,到菜场取奶和买菜。接着,步行去单位处理一件公务。然后,因为半夜里曾感到胸闷难受,医院看病。一检查,广泛性心肌梗塞,立即抢救,同时下了病危通知。中午,他对守在病床旁的大弟说,不要大惊小怪,没事的。他真的不相信他会死。可是,一小时后,他就停止了呼吸。 父亲终于没能看到我的孩子出生。如我所希望的,我得到了一个可爱的女儿。谁又能想到,我的女儿患有绝症,活到一岁半也死了。每想到我那封报喜的信和父亲喜悦的回应,我总感到对不起他。好在父亲永远不会知道这幕悲剧了,这于他又未尝不是件幸事。但我自己做了一回父亲,体会了做父亲的心情,才内疚地意识到父亲其实一直有和我亲近一些的愿望,却被我那么矜持地回避了。 短短两年里,我被厄运纠缠着,接连失去了父亲和女儿。父亲活着时,尽管我也时常沉思死亡问题,但总好像和死还隔着一道屏障。父母健在的人,至少在心理上会有一种离死尚远的感觉。后来我自己做了父亲,却未能为女儿做好这样一道屏障。父亲的死使我觉得我住的屋子塌了一半,女儿的死又使我觉得我自己成了一间徒有四壁的空屋子。我一向声称一个人无须历尽苦难就可以体悟人生的悲凉,现在我知道,苦难者的体悟毕竟是有着完全不同的分量的。 (本文选自《守望的距离》,周国平著。) 妈妈老了龙应台二十岁的时候,我们的妈妈们五十岁。我们是怎么谈她们的? 我和家萱在一个浴足馆按摩,并排懒坐,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一面落地大窗,外面看不进来,我们却可以把过路的人看个清楚。 这是上海,这是衡山路。每─个亚洲城市都曾经有过这么一条路──餐厅特别时髦,酒吧特别昂贵,时装店冷气极强、灯光特别亮,墙上的海报一定有英文或法文写的“米兰”或“巴黎”。最突出的是走在街上的女郎,不管是露着白晰的腿还是纤细的腰,不管是小男生样的短发配牛仔裤还是随风飘起的长发配透明的丝巾,一颦一笑之间都辐射着美的自觉。她们在爱恋自己的青春。 家萱说,我记得啊,我妈管我管得烦死了,从我上小学开始,她就怕我出门被强奸,每次晚回来她都一定要等门,然后也不开口说话,就是要让你“良心发现、自觉惭愧”。我妈简直就是个道德警察。 我说,我也记得啊,我妈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放肆”。那时在美国电影上看见演“母亲”的讲话轻声细气的,浑身是优雅“教养”。我想,我妈也是杭州的绸缎庄大小姐,怎么这么“豪气”啊?当然,逃难,还生四个小孩,管小孩吃喝拉撒睡的日子,人怎么细得起来?她讲话声音大,和邻居们讲到高兴时,会笑得惊天动地。她不怒则已,一怒而开骂时,正气凛然,轰轰烈烈,被骂的人只能抱头逃窜。 现在,我们自己五十多岁了,妈妈们成了八十多岁的“老媪”。 “你妈时光会错乱吗?”她问。 会啊,我说,譬如有一次带她到乡下看风景,她很兴奋,一路上说个不停:这条路走下去转个弯就是我家的地,或者说,你看你看,那个山头我常去收租,就是那里。我就对她说,妈,这里你没来过啦。她就开骂了:乱讲,我就住在这里,我家就在那山谷里,那里还有条河。 我才明白,这一片台湾的美丽山林,彷佛浙江,使她忽然时光转换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她的眼睛发光,孩子似的指着车窗外,佃农在我家地上种了很多杨梅、桃子,我爸爸让我去收租,佃农给我一大堆果子带走,我还爬很高的树呢。 你今年几岁,妈?我轻声问她。 她眼神茫然,想了好一会儿,然后很小声地说,我……我妈呢?我要找我妈。 家萱的母亲住在北京一家安养院里。开始的时候,她老说有人打她,剃她头发,听得我糊涂──这个安养院很有品质,怎么会有人打她?家萱的表情有点忧郁,“后来我才弄明白,原来她回到了文革时期。年轻的时候,她是工厂里的出纳,被拖出去打,让她洗厕所,把她剃成阴阳头──总之,就是对人极尽的污辱。” “后来想出一个办法。我自己写了个证明书,就写某某人工作努力,态度良好。” 我不禁失笑,怎么我们这些五十岁的女人都在做一样的事啊。我妈每天都在数她钱包里的钞票,每天都边数边说我没钱,我的钱到哪里去了。我们跟她解释说她的钱在银行里,她就用那种怀疑的眼光盯着你看,然后还是时时刻刻紧抓着钱包,焦虑万分。怎么办? 我于是打了一个银行证明:兹证明某某女士在本行存有五百万元,然后下面盖个方方正正的章,红色的,连盖好几个,看起来很衙门,很威风。我交代印佣:“她一提到钱,你就把这证明拿出来让她看。”我把好几幅老花眼镜也备妥,跟银行证明一起放在她床头抽屉。钱包,塞在她枕头下。 按摩完了,家萱和我的“妈妈手记”技术交换也差不多了。落地窗前突然又出现一个年轻的女郎,宽阔飘逸的丝绸裤裙,小背心露背露肩又露腰,一副水灵灵的妖娇模样;她的手指一直绕着自己的发丝,带着给别人看的浅浅的笑,款款行走。 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心中有一分明白,月光泻地。 (本文节选自《目送》,龙应台著。) 我的父亲母亲:逝者已经逝去,活着的还要前行任正非(华为)谈及华为任正非、联想柳传志这些科技公司的大佬,总会让人油然而生一股尊敬感,作为国内互联网行业的前辈和先驱,如今他们已经站在这个行业的顶端,居高临下的地位让很多人羡慕不已,但是不要忘了,他们在摸索前行中经历的苦难也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下面,我们就通过华为任正非的《我的父亲母亲》来感受下那一代人所经历的辛酸苦楚。文是老文,却依旧值得细细品味。另附联想柳传志的读后感,同样值得一读。 上世纪末最后一天,我总算良心发现,在公务结束之后,买了一张从北京去昆明的机票,去看看妈妈。 买好机票后,我没有给她打电话,我知道一打电话她一下午都会忙碌,不管多晚到达,都会给我做一些我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直到飞机起飞,我才告诉她,让她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车来接,我自己坐出租车回家,目的就是好好陪陪她。 前几年我每年也去看看妈妈,但一下飞机就给办事处接走了,说这个客户很重要,要拜见一下,那个客户很重要,要陪他们吃顿饭,忙来忙去,忙到上飞机时回家取行李,与父母匆匆告别。妈妈盼星星、盼月亮,盼唠唠家常,却一次又一次地落空。 回到昆明,就知道妈妈不行了,她的头部全部给撞坏了,当时的心跳、呼吸全是靠药物和机器维持,之所以在电话上不告诉我,是怕我在旅途中出事。我看见妈妈一声不响地安详地躺在病床上,不用操劳、烦心,好像她一生也没有这么休息过。 我真后悔没有在伊朗给妈妈打一个电话。因为以前不管我在国内、国外给她打电话时,她都唠叨:“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身体还不如我好呢”,“非非你的皱纹比妈妈还多呢”,“非非你走路还不如我呢,你这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病”,“非非,糖尿病参加宴会多了,坏得更快呢,你的心脏又不好”…… 我想伊朗条件这么差,我一打电话,妈妈又唠叨,反正过不了几天就见面了,就没有打,而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如果我真打了,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妈妈就躲过了这场灾难。这种悔恨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我看了妈妈最后一眼,妈妈溘然去世。 年,我父亲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塑料包装的软饮料,喝后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 父亲任摩逊,尽职尽责一生,可以说是一个乡村教育家。妈妈程远昭,是一个陪伴父亲在贫困山区与穷孩子厮混了一生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园丁。 父亲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一头扎进去就是几十年,他培养的学生不少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有些还是中央院校的校级领导,而父亲还是那么位卑言微。 我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今天想来还历历在目。 我们兄妹七个,加上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来源。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要交2-3元的学费,到交费时,妈妈每次都发愁。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 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还穿着厚厚的外衣,就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衬衣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我家当时是2-3人合用一条被盖,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 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我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我们家当时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如果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个、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高三快高考时,我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着吃,被父亲碰上几次,他心疼了。其实那时我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缸装着,我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 高考前三个月,妈妈经常在早上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要我安心复习功课,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就进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背负着这种重托,我在当时的环境下,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学习了逻辑、哲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终因我不是语言天才,加之在军队服务时用不上,20多年荒废,完全忘光了。 我当年穿走父亲的皮鞋,没念及父亲那时是做苦工的,泥里水里,冰冷潮湿,他更需要鞋子。现在回忆起来,感觉自己太自私了。 回顾我自己已走过的历史,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 爸爸,妈妈,千声万声呼唤你们,千声万声唤不回。 逝者已经逝去,活着的还要前行。 (本文来源于《意林》杂志) 标题为编者所加,图片来源于网络。赞赏 长按北京哪家治疗白癜风的医院最好白癫风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
节日失去后才明白,不要让亲情留遗憾
发布时间:2018-5-6 0:06:31 点击数: 次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张阿泉一个人的读书月下
- 下一篇文章: 喜欢阅读的孩子差不到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