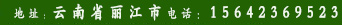|
第一个故事 几年前搬家,书们被从架子上一一取下,捆扎,打包。 家中书架一直采取敞开式,沿墙顶天立地,不设背板亦无柜门,如此可节约一点空间。 一小段紧靠墙壁的书,书脊霉得一塌糊涂,或许那儿曾经泼倒过一杯茶水而不知。 发霉的书集中在一套名为“曼陀罗”的散文文丛,有十几本,小32开,封面灰白色,装帧寒素。这套书买了总有十年,竟从未一一翻阅。说起来,书架上没看的书岂独它们。如今既已霉味扑鼻,心下就想扔了算了。 一直像个老奶奶似的舍不得扔东西,那就从这套书开始练习吧……我蹲在地上,随手翻开其中的一本,想做一个最后的判断……刚刚看了几行,改蹲姿为正襟危坐了。 翻开的那篇文章是谈论繁体字和简体字的。因有人大代表提出恢复繁体字,这个话题近年正变得有点时髦,但作者写此文显然与此无关,因这套书出版于年。他对这个问题的识见,拿到时髦的今天依然显得卓越。文章博古通今,侃侃而谈,一篇读下来,除长不少知识更有惊艳之感——当今中国,谁有这般学问见解,又有这闲庭信步般清谈的气度,还有这么一手好文章? 脑子里电光火石冒出一名字:阿城。只有阿城有这本事。 赶紧到封面去看作者名,是一个一看即为笔名、没有见过的名字。 但是,从行文笔触判断,这本书绝不可能出于籍籍无名之辈。 试图从前言后记中寻找蛛丝马迹。前言只有林贤治先生的总序。后记出自作者之笔,温文,节制,深情。但关于生平毫无线索可攀附。 唯有从文章中觅到的只言片语,知作者目前长居国外,青年时代下过乡插过队。这两点亦都与阿城合。书中多数文字,并非谈论繁简字这一类,更多是夜深人静剖明心迹,内敛,安静,时有忧伤孤愤。 我知阿城为异人,他的两本书《闲话闲说》与《威尼斯手记》早已绝版,无数出版商想重做,他均不允,宁让它们绝迹。如此说来,做出此等隐姓埋名著书之事亦非他莫属了。 像一个侦探一样进行一番推理后,我颇自得地以为寻找到了答案。并为此再次迷上阿城,旋即到网上搜罗他的文字,重读《棋王》《孩子王》——真是炉火纯青之作啊。 能找到的阿城文字相当有限,而我竟意外发现他不肯以真名示人的作品;阿城给我印象是闲云野鹤般高蹈,这本书中的“阿城”,却是那么沉郁深情,至情至性——好像我偷窥了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那种感觉真是相当奇妙啊。 事实上呢,如上感慨均不成立,我是一个蹩脚的侦探——此书非阿城著,作者是一位诗人,早年即移居国外。 第二个故事 页,书脊厚度约0.8厘米,定价8元,一本绿色封皮的朴素小册子,年,我在凤凰台楼下凤凰书城四楼外国文学专柜发现了它。六本竖列在一起,依然谈不上任何阵仗,不起眼地瑟缩在一个角落。 先买了一本。看完后一气买了三本,分赠了妈妈和两位写作的朋友陈蔚文、鲁敏。动员亲密小朋友小羽买了一本。想着还留一本何苦让它落单,跑去把最后一本买来,心安了。 这个封面丑得让人无语,但还是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是俄裔美籍作家谢尔盖·多甫拉托夫。他生活在苏联时代,是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者与不合作者,被驱逐到美国。 全书十三章,每章写一位家人,每章都是一篇迹近完美的短篇小说,集合在“我们一家人”这一标题之下,组成一本薄薄的长篇小说。 看来作者偏爱这种结构方式,他的另一本书《手提箱》有类似结构,以手提箱统领,每一章叙述手提箱中一样物事,用事物串联起思绪、记忆、岁月……一个从俄国带到美国的手提箱变成五味杂陈的生活本身,一个会呼吸有生命的有机体。 对了,作者还极度偏爱省略号。《我们一家人》是一本充满省略号的书。无论看多少遍,我都觉得意犹未尽。 说一下我特别喜爱的段落吧,比如关于姨妈的故事。 姨妈是位美人,一生中曾被热烈爱过。职业是出版社编辑,一辈子在为别人编书,接受过众多知名作家的感谢。当然,无论爱情还是谢意最后都什么也不是。晚年她读很多书,而她一死藏书立刻被卖光。姨妈纷繁热闹的一生,其实什么都没剩下。 姨妈去世前,曾给“我”念一首诗: 生命已到中途 而我一直以为,自己可以撼动大山 我可以在田野播种,在谷底浇灌 而生命早已过半…… “一位女诗人的诗。”姨妈笑了。我觉得是她自己写的。当然,词句粗浅。第一行就是引用了但丁的话。不过,它还是令我感动。 生命已到中途而我一直以为,自己可以撼动大山 作者随即写道: 姨妈错了。生命已经接近终点。更改错误已经不可能了…… 姨妈错了……生命已经接近终点……更改错误已经不可能了……这是振聋发聩的三句话,我无法形容其中的痛悔与绝望。而这种悔恨,很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轮到品尝。 我想到我的妈妈,她曾说:“刚开始有一点懂得生活,想好好生活,就已经老了,什么都来不及了……”我在电话线这头听着,在电流的嘶嘶声中保持沉默,因为知道这巨大伤感是无从安慰的。她在说一个事实。我唯一能做的是和她一起面对这个事实。面对,是最后的勇敢与尊严。 我想到我自己,在许多时候并不曾好好生活。荒废过许多光阴。立下种种计划。还在为未来筹措。想要的生活似乎仍在远处等我。这一切会不会是姨妈般的错觉?我们永远以为生命尚在途中,而终点的来临并不事先张扬通告…… “姨妈错了……”我没有读过比这更沉痛的话。 第三个故事 有一年去浙江诸暨参加一个笔会,我、陈蔚文、庞培诸人(记得还有赵彦、陈东东、周美丽以及陪同的小娄)游了五泄,准备往千柱屋去。途中停下来吃饭。 吃饭的地点类似农家饭庄。进门一方正大庭院,四边有回廊,我们的饭桌就设在回廊靠大门处。特地拣了个位置,可以看到门外的柳树。五月的风蹿来蹿去,人不免气定神闲起来。 只有我们这一桌食客,大家等上菜,这当儿聊到读书。 我提起《我们一家人》。我以为没人知道它。 但是庞培作思索状,随即说:“啊,《我们一家人》,就是《手提箱》那个作者写的,谢尔盖·多甫拉托夫对不对……” 我惊喜:“就是他!”(像发现了一个重案犯。) 我:“从作者介绍中看到他还写过《手提箱》,一直想找来看却找不到,还以为国内没有翻译过来呢……” 庞培:“有译本的。我写过一篇《手提箱》的读后感,回头发给你。” 继续聊天。我自得地说到很可能发现了一本阿城的佚作——把整个过程详细叙述了一遍。 庞培若有所思地说:“你这个故事有点意思……” 我受宠若惊,因从没意识到这点小经历可以称为一个故事。 他接着说:“……是有这种情况,在完全没有想到的时候与一本书相遇。” 回南京后,我收到他发来的《读手提箱》,读完恍然大悟:原来《手提箱》亦是他的偶遇。 读《手提箱》(节选) ·庞培 雨是说下就下。有一次我就这样被困在书店里,买了这样一本名叫《手提箱》的书。 在雨中一个人可以买回来多少名字稀奇古怪的书嗬!但是我敢打赌没有比《手提箱》更古怪的书名的了。印象中这本薄得不起眼,装帧完全离谱的小说放在书店的夹层起码也有四年了。因为我曾分别把它邂逅相遇的左、右姐妹一次次买走。我在这一层架子上淘回过不少好书,惟独每次都只看一看它,拿在手上翻一下,鼻子闻闻,有几次甚至懒得伸手去碰它。我是书店的研究者,自信从不会有好书得以逃脱我的眼睛。可是俗话说:“人算算不过天算”。读者既便具有鹰隼般锐利的嗅觉,老天也常把他们的所谓聪明(智慧)化为粪土。这一次,在这一本名字并不讨喜的书上,我又犯了多么轻率的可爱毛病! ……这本薄薄了不起的小书放在这里,一直在耐心等待人们发现并进入它,每一次待我进来,清醒、傲慢、无聊、吃了酒……走近这一排架子,它都在无声地向我们诉说,直至前不久的这一场雨,使我感到我这一生是多么的矛盾和失败,并最终把它送到收银台,这真是了不起的我和《手提箱》或作家谢尔盖·多甫拉托夫(—)之间可以相互额手称庆相贺喜的一天。我终于没有失足到底,给了在不容错失的好书上一个挽救自己的机遇。 我在雨中把它挟回家,只读了前二十分钟不到就惊喜莫名,拍案大叫起来。人们是如何称赞这样的称心快事的呢?书和读者,互相视若知己。成语说“视如己出”,也就是这个意思了吧。我简直。难以。但又。恐怕。不得不。无法。因为在美丽的事物(造物)面前,人类的语言总是不够。 “真正的书读我们。”世上的人只知道海明威,有谁知道(像一星期前的我)谢尔盖·多甫拉托夫?“文革”时,中国人发明了一种说法:“一小撮”,这真是绝妙的说法。世上的人只知道海明威,但有少量的(迹近于一小撮)人还顺带知道《骑兵军》作者巴别尔,但又有谁(我再说一遍!)知道这之外还另有一个谢尔盖·多甫拉托夫! 我提海明威,《手提箱》的作者定要骂我,甚至不屑(这我心知肚明)。但我确实在他这里,读到了跟海明威一样好的简洁、犀利,一样硬的男性风格,但却更简洁和更犀利,并且,重要的是:更加的美妙! 作者跟布罗茨基是好友,一样蹲过苏联的监狱,一样被驱逐出境,但却英年早逝。《手提箱》中译本第3页,他说:“我看着空箱子,布罗茨基在上,卡尔·马克思在下,而位于其间的是一去不复返的生活,珍贵无比而又绝无仅有的生活。” 教育不仅教给孩子们知识,更重要的是打开他们的心智。我希望通过写作教会孩子们开启一种个性化的生活。欢迎来到章红写作课堂,搜索公众iting,或长按下图 赞赏 人赞赏 哪家白癜风能彻底治愈中科医院白癜风诊疗康复标准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wyszentea.com/lsjf/1217692.html |
读书像破案与书相遇的三个故事
发布时间:2018-5-9 19:05:11 点击数: 次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友情传递绿色生活北京市八一学校保定分
- 下一篇文章: 创建绿色校园,拥抱绿色生活记小学部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