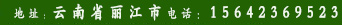|
日本自年第一次斩获诺贝尔奖以来,累计已有0余位诺贝尔奖得主。年,日本出台“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提出“50年要拿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当时,从日本国内到国际社会,对此争议都不小。可从到年,日本平均一年拿下一个诺奖。也有数据表明,日本近些年的科研发表数量呈下降趋势,被引用的数量也没有以前多。狂揽诺奖的日本人,危机感还是很重,其实没别人想象中那么高兴。回到年,日本政府提出了个“豪气干云”的科技计划——要在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计划执行了19年,获诺奖的日本人已有19位。从结果来看,这个目标不但不傻,还十分保守了。日本在科学界的成果如此亮眼,引起了他国的艳羡。尤其是邻国中国,关于日本诺奖的文章不计其数,有呼吁学习模仿日本的,也有反省批判本国教育制度的。日本的声音主要并非总结成果,而是反省和居安思危。他们认为,获奖的人多是年事已高的老研究者,他们手中的多是0年前的科研成果。而更多的学者提到了眼下学界人才寥寥、青年人不愿投身科研的现状,推断接下来日本会进入“诺奖荒”,不少人呼吁政府对学界松绑,鼓励青年参与。可道是,学霸学习好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不知足,还挑灯夜战。1时间的检验回顾日本近0年的诺奖成就,集中在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三大领域。统计下来,年以后的日本诺奖获得者的获奖成果,大都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前后取得的,比他们获诺奖时间要早二三十年。拿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京都大学教授本庶佑来说,他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研究免疫抗体,他的主要成果是年获得的,从出成果到拿诺奖,等了6年。△本庶佑这里必须提到诺奖的评选特性之一——可靠性。科学往往是不断推翻前人论述的结果,牛顿推翻了传统力学,爱因斯坦推翻了牛顿力学。某种程度上来说,科学充满了后人对前人的“打脸”。诺贝尔奖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打脸”。年的化学奖发给莫瓦桑,原因是他合成出了人造金刚石,但后来发现是助手搞出的乌龙骗局。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发给莫尼斯,原因是他发现了脑白质切断术对某些精神疾病的治疗价值,然而这种具有严重副作用的疗法后来被禁止了。△莫尼斯杨振宁和李政道在提出“宇称不守恒”的第二年就获诺奖,这属于特例。研究成果是否可靠,需要时间的检验。在自然科学领域,这个时间多为0年以上。本庶佑也坦言,科研之路是非常漫长的,尤其是基础研究。他说,研究成果要回馈社会耗时较长,又长期得不到认可,这对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产生很大影响。他期待社会更加宽容地对待基础研究。△杨振宁和李政道基础研究苦,放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诺贝尔奖的设立,正是用来激励那些把青春奉献给科学事业、并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们。良好的科研环境与生源质量回归到为何日本能在这0年如同“井喷”式地产出诺奖,就要溯源到几十年前。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脱不开关系,你很难看到一个穷国长出显眼的科技树。日本战后经济年均10%的高速发展,给科技发展提供了坚强后盾。年,日本在制订“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同时,还制定了与此目标相呼应的“振兴科学技术的综合基本政策”,提出要力争将国民收入的%用于科研。充沛的资金吸引了优秀人才,也带来了先进的实验仪器与富足的科研经费。△年代的日本商铺到了70年代,出口经济蒸蒸日上的日本,逐渐打响了MadeinJapan的旗号。凭借物美价廉的产品,日货为本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政府进一步提高了科研支出比例,目标将国民收入的3%用于科研。到了年,日本的研发经费已经超过了法、英两国的研发经费之和,正式步入科技大国的行列。教育改革是日本科技腾飞的另一关键因素。来到今天的日本,你会发现一件特别的事:别看日本国土面积小,但是大学格外的多。国立和公立自不必说,私立大学多如牛毛。不同于普通人对大学校园的印象,有些私立大学并无校园,只有一栋楼作为教学场所。年,中央教育审查会议向文部省提出了题为“关于改善大学教育”的咨询报告。报告里提出的诸如扩大教育规模、增设理科类的高等教育机构等建议,对后来的日本大学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东京大学其结果突出表现在,年至年间,日本高等教育机构的总数从55所增加到91所,增加了75%。学校增多了,大学生自然也多了。日本并非僧多粥少,而是僧少粥多,有些大学都招不到人,为生源而发愁。70年代的大学生比前十年多出了.4倍,大学俨然一副“全民教育”的样子。更多的青年人进入大学,自然也就有更多的人投身科研。科研成果的最佳证明是什么?自然是论文数量。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年日本在五个科学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为篇,仅次于发表数量为篇的美国,位列世界第二。再仔细观察下,你可以发现,日本的诺奖获得者多集中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等国立综合大学。这几所大学都为战前的“帝国大学”(七帝大: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东北帝国大学、九州帝国大学、北海道帝国大学、大阪帝国大学、名古屋帝国大学)。△京都大学战时沦为各类武器制造场所的帝国大学,在战后被改造为以研究为主的国立综合大学。不少国立大学都崇尚学风自由、研究至上的观念。这从侧面说明一件事,除了“全民教育”潮流提升民众整体素养,更优秀的日本国立大学的科研环境与生源质量,是可以培养出诺奖得主的。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之后,研发经费投入不断增大,这为科技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大学扩大教育规模、调整学科结构与青年学生的增多等因素综合起来,为日本诺奖的产出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3不拘一格的诺奖得主斩获诺贝尔奖不易,每位得主都有自己的个性,不拘一格。日本的诺奖获得者,尤其有着许多“不正常”的经历。“皆为利往”的时代,日本的科研者却总带着一种特殊气质。年,日本的下村修阴差阳错发现“绿色荧光蛋白”,他的研究成果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他说:“我做研究不是为了应用或其他任何利益,只是想弄明白水母为什么会发光。”在他看来,获得这项殊荣不过是在满足自己好奇心的路上,顺便完成的一件事情。△下村修00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田中耕一,经历更有趣。当时诺奖的报道一出,整个日本的媒体都陷入了“寻找田中耕一”的模式。△田中耕一似乎没有什么人听说过“田中耕一”的名字,所有的数据库里也未曾录入过与他相关的信息。直到后来,人们发现,他只不过是一家企业里的无名小卒。田中耕一不是什么专业的教授,也不是硕士博士出身,他是一间普通大学电气工程专业毕业的本科生。毕业后他一直在一家仪器制造会社担任电气工程师,获奖前,甚至连一篇像样的论文也没发表过。人到中年,他却从电气转到化学领域,研究出对生物大分子的质谱分析法,拿下了诺奖。低学历、跨专业,从来不是日本科研者自暴自弃的借口。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中村修二,身份背景同样平淡无奇。他出生在日本一个小渔村,从小就被别人叫“笨小孩”,高考也只考上了排名没那么好的德岛大学。△中村修二毕业之后,中村修二进入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工作。安于现状,他也就只能在公司里待到退休。他在公司里研发的成果销量一般,经常被同事嘲笑是“吃白饭”的,连上司都问他:“你怎么还没有辞职?”满腔怒气促使他开始了疯狂的努力,挑战一项看似无法达成的任务:开发高亮度蓝色的LED。在这项研究上,有无数人前仆后继,却也有无数人失败而返。当所有人都觉得中村修二不行时,他只是回答,“可以的”。与来自专业背景的人不同,中村修二就像野蛮生长的局外人,他撇开专业“常识”,在自己开拓的道路上默默耕耘,最终开发出蓝色LED技术,赢得诺贝尔奖。中村修二说:“愤怒是我全部的动因,如果没有憋着一肚子气,我就不会成功。”除了低学历之外,日本的诺奖得主中还有一位出了名的外语文盲——益川敏英,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在大学时期,益川敏英的英语就时常垫底,无论他如何努力,英语的水平和兴趣都从来不见起色。因为这个,益川敏英不敢轻易往外跑,拒绝参加许多国外的研讨会,在斯德哥尔摩领奖之前,他从未踏出过日本国门。△益川敏英获得诺贝尔奖后,他用日语发表感言。会后有记者问他:“您打算学英语吗?”这位老教授干脆地回答:“不。”这大概就是这位科研者最后的坚守。比起许多国家的诺奖得主华丽的履历,日本的研究者们看似更加接地气,来自五花八门的领域、背景,不那么完美的经历,更让人看到,日本这个国家在科研领域注入的国民性。4日本人的危机感日本政府每年都会公布《科学技术白皮书》,对日本的科研实力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并和全球主要国家进行比较。年的白皮书指出,日本推动创新的基础能力正在迅速减弱。△日本政府公布的《科学技术白皮书》其中,显示研究质量的“被多次引用的学术论文篇数”一项,日本在各个国家中的排名已从10年前的第4位下降至第9位。即使是每年都有人拿诺贝尔奖的日本,仍认为,肩负下一代未来的年轻研究人员,境遇更加困难。他们深知,想要持续创造国际性研究成果,就必须怀着危机感推进各项改革。所以从年以来,日本《科技白皮书》多次承认日本科技创新力出现衰退,不论是论文的数量质量还是科研人才储备,以及研发资金投入都表现不佳。就算诺奖拿到手软,日本“高兴不起来”的原因,不只是危机意识,更是现实问题。日本人重视荣誉,却在狂揽诺奖时,保持着令人生畏的冷静。5做到极致的匠人精神极致认真、脚踏实地、耐得住寂寞、确定一个目标就执行到底的匠人精神,是日本文化中不容小觑的一项。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大隅良典,为诺奖足足等了二十年。在此前长达二十多年的学术长跑里,他经历了种种挫折:博士毕业没工作、研究得不到支持、被迫转专业……但他仍坚持缩在实验室里专心致志于自己的研究,“十年如一日”熬过枯燥的学术生活。△大隅良典从小处看,匠人精神是一种踏实,吃苦耐劳,是对细节的严谨执着;从另一方面,也是在科学精神方面的专业。一位留日的科研工作者说:日本科研工作者在实验室的小组研讨会上会非常细致认真地研讨错误出现的原因,但不会对研究者本人提出任何批评。这种对待错误的严谨和对出错者的宽容,恰恰激励了人们更加重视错误,防止错误的再发生。正是匠人精神中矢志不渝的专注力量,才为创新发现时的灵光乍现提供可能,同时,为观点的实现提供保障。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曾说:“保持孤独,我才能够不被这些东西左右,逼近事物的本质,这让我能产生新的点子。”在他看来,保持孤独,才能从内挖掘能量;专注于自身,才能缩短减少接触到“事物的本质”的时间,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换来的恰恰是灵感迸发的瞬间。而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之间的运筹帷幄,也演绎着日本文化中的“菊与刀”。“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看似急功近利,但同时,日本人已经用几十年来的踏实付出为此做好准备。美籍华裔科学家陈列平在肿瘤免疫治疗的研究中,首先提出了通过抗PD-1通路抗癌的思路。却一直没有拿到诺奖,许多科学界内人士为他鸣不平,认为诺奖评审不公。但陈列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中国人不擅长讲故事,不擅长将复杂的科学变为简单的概念去让人们接受,这一点可能是我们最大的缺陷。”在日本进入1世纪后这些突出的成就中,也可以让人看清,在更多方面,也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搞科研需要投入,需要人才,需要灵光一现,需要开放交流,但更重要的是有足够耐心。在中国对科研投入逐年增长的今天,或许这是日本给中国最大的启示——有了耐心,离诺奖“井喷”的那天也就不远了。 长按
|
教育资讯日本21世纪屡拿诺贝尔奖,给我
发布时间:2020-7-23 17:20:28 点击数: 次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直销生活化21世纪的商机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